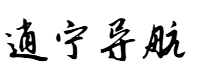山村野花开_山村野花开最新章节_情满月出_笔趣阁
itomcoil 2025-10-27 15:29 2 浏览
那只包裹是傍晚送到的,没有署名,只有一个模糊的、来自南方的邮戳。
我,陈敬明,七十二岁,退休的大学历史系教授,正坐在书房里,校对我那本关于明代水利工程的专著终稿。
窗外下着雨,不大,但很密,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灰色纱网,把整个世界都罩得有些不真切。
我用裁纸刀划开包裹的胶带,动作很慢,手腕处的老年斑像褪色的地图。
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木盒子,樟木的,散发着一股被时间封存的、沉静的香气。
盒盖没有锁,我轻轻一掀就开了。
里面躺着一枚小小的、雕工粗糙的木鱼。
还有一张泛黄的旧照片。
照片上,一个女人抱着一个约莫四五岁的男孩,背景是茫茫的水面和远山。
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,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。
她没有笑,但嘴角有种向上提起的、坚韧的弧度。
男孩很瘦,眼睛却黑亮得惊人,直直地看着镜头外,仿佛在看我。
我的呼吸停滞了一瞬。
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,然后缓慢地、痛苦地收紧。
是她,林水云。
还有那个孩子,水生。
不,他后来不叫水生了。
思绪像决堤的洪水,瞬间冲垮了我用三十多年光阴辛苦垒砌的堤坝,把我卷回了那个潮湿、闭塞、只有水声和风声的山村水库。
那一年,我三十五岁。
一九七六年,我作为“待清查的反动学术权威”,被从大学的讲台上直接“下放”到了青龙山水库。
那是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偏僻地方。
送我来的吉普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,最后停在了一排灰扑扑的平房前。
水库管理处的主任姓王,是个粗壮的汉子,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件需要小心处理的危险品。
“陈敬明,”他对着手里的文件,念出我的名字,语气生硬,“以后你就住这儿,负责看守五号闸门,顺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”
他指向不远处水边的一栋独立的小泥屋。
“那儿,林水un家。她男人前年修水坝的时候掉下去,没上来。家里就她跟一个娃。你住她家西边那间,跟她家就隔一道帘子。互相监督。”
“互相监督”四个字,他说得格外重。
我拎着我那只破旧的行李箱,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,全是书。
我走向那栋小泥屋,脚下的泥土湿滑黏腻,空气里满是水汽和不知名野草腐烂的味道。
门是虚掩的。
我推开门,一股潮湿的霉味混杂着淡淡的烟火气扑面而来。
屋里很暗,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。
一个女人正背对着我,在灶台前忙碌。
她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蓝布褂子,身形单薄,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倒的芦苇。
听到动静,她回过头。
就是照片上的那张脸,只是年轻了许多,也憔悴了许多。
她的眼睛很静,像水库深处的水,看不出什么情绪。
“你是陈同志吧,”她开口,声音很低,也很轻,“王主任打过招呼了。西屋我收拾出来了,你住吧。”
她指了指左手边用一张破旧床单隔开的空间。
那就是我的“房间”。
一张木板床,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,没了。
我把行李箱放在墙角,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吃饭吧。”她没有多看我,转身从锅里盛出两碗东西。
是红薯粥,稀得能照见人影,上面飘着几根咸菜。
她把一碗推到我面前,自己端着另一碗,坐到小板凳上,又把一个更小的碗放在地上,里面是粥和捣碎的咸菜。
一个瘦小的孩子从门后探出头来,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,然后跑到女人身边,蹲在地上,小口小口地吃起来。
那就是我们的第一顿饭。
沉默的,压抑的。
我能感觉到那孩子好奇又警惕的目光,像只小兽。
而那个女人,林水云,自始至终没有再跟我说一句话。
她只是吃,然后收拾碗筷,整个过程安静得像一幅静物画。
晚上,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,听着隔壁传来的轻微呼吸声,还有窗外水库永不停歇的拍岸声。
哗啦,哗啦。
那声音像时间的叹息,要把人所有的意志都磨碎。
我睁着眼睛,看着屋顶的黑暗,感觉自己像被活埋了。
我和林水云的“同居”生活,就这样在一种诡异的平静中开始了。
我们像两条生活在同一个鱼缸里却互不相干的鱼。
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烧水,做饭,然后去水库的养殖场干活,或者上山采草药、挖野菜。
孩子叫小山,总是跟在她身后,像条小尾巴。
我则每天去五号闸门报到,工作很简单,就是记录水位,清理一下闸口的杂物。
大部分时间,我都是一个人坐在闸门边,对着茫茫的水面发呆。
我们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。
这堵墙,是身份的鸿沟,是世俗的偏见,是那个时代强加给我们的隔阂。
我是一个从城里来的、戴着“帽子”的知识分子。
她是一个偏远山村的、无依无靠的寡妇。
我们被强行捆绑在一起,成了彼此生活中的一个尴尬存在。
村里的人看我的眼神是鄙夷和警惕的。
看她的眼神,则多了几分暧昧和嘲讽。
我偶尔能听到一些风言风语。
“一个寡妇家,住进个城里来的男人,像什么话。”
“还是个‘坏分子’,指不定安的什么心。”
林水云对这些话置若罔闻。
她就像水库边上的一块石头,任凭风吹雨打,浪花拍击,始终沉默着,坚硬着。
我们之间唯一的交流,是饭桌上的碗筷碰撞声。
她会把饭菜做好,给我留一份在锅里。
我吃完,会自己把碗洗干净。
这是一种默契,一种小心翼翼维持的、脆弱的平衡。
我试图保持我最后的尊严。
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点上一小截蜡烛,偷偷看我带来的那些书。
那些文字,是我唯一的慰藉,是连接我与过去那个文明世界的最后一条线。
有一次,我看得太晚,被她起夜时发现了。
她站在帘子那边,身影在昏黄的烛光下显得模糊。
我以为她会去告发我。在当时,这些书都是“毒草”。
但她只是沉默地站了一会儿,然后轻轻说了一句:“费油。”
说完,就转身回去了。
第二天,我的桌上多了一盏小小的煤油灯,灯油是满的。
我看着那盏灯,心里五味杂陈。
我不知道她是出于同情,还是别的什么。
但那一刻,我感觉我们之间的那堵墙,似乎有了一丝裂缝。
转折发生在一个暴雨的夜晚。
山里的雨说来就来,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的瓦片上,噼里啪啦,像要将这间小泥屋吞噬。
我白天在闸口巡查时淋了雨,晚上就开始发高烧。
我躺在床上,浑身滚烫,骨头像散了架一样。
意识在清醒和模糊之间摇摆。
我感觉自己像一条搁浅的鱼,在绝望地等待死亡。
迷迷糊糊中,我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。
然后,是她焦急的声音,第一次带了情绪:“陈同志?陈同志!你醒醒!”
我努力睁开眼,看到林水云的脸就在我上方。
她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了,几缕贴在脸颊上,眼神里满是担忧。
“你发烧了,烧得很厉害。”她说,“得请个医生。”
“没用的,”我声音嘶哑,“这种地方……哪有医生。”
“有!我去叫!”
她说完,抓起一件蓑衣就冲进了雨里。
我看着她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。
我们非亲非故,甚至算得上是“阶级敌人”,她为什么要这样为我?
不知过了多久,她带着一个背着药箱的老人回来了。
两人浑身都湿透了。
老人给我扎了针,又开了一些草药,嘱咐了几句就走了。
林水云把草药熬好,一口一口地喂我喝下。
药很苦,苦得我舌根发麻。
但那股暖流顺着喉咙流进胃里,却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暖意。
那一夜,她没有回自己的床。
她就坐在我的床边,时不时用湿毛巾给我擦拭额头和手心。
我烧得迷迷糊糊,总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,生病时母亲也是这样守着我。
后半夜,我退了烧,人也清醒了一些。
我看到她趴在床沿睡着了,眉头依然紧锁着。
煤油灯的火苗轻轻跳动,映着她清瘦的脸。
我第一次这么近地、这么仔细地看她。
她的皮肤因为常年劳作而显得粗糙,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。
但她的眉眼很清秀,鼻梁很挺,嘴唇的形状很倔强。
这是一个被生活磨砺得失去了光彩,但依然保留着风骨的女人。
那一刻,我心里那点可怜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优越感,彻底崩塌了。
在她面前,在她的善良和坚韧面前,我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。
天亮时,她醒了。
看到我睁着眼睛,她有些不好意思,连忙站起来。
“你好些了?”
我点点头,挣扎着想坐起来。
“谢谢你。”我说,声音还有些沙哑。
她摇摇头,转身去给我倒水,低声说:“你是个好人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好人”这个词,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。
从我被下放的那天起,我就是“坏分子”、“牛鬼蛇神”,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。
她是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,说我是“好人”的人。
我看着她的背影,眼眶有些发热。
那场病,像一场洗礼,冲刷掉了我们之间大部分的隔阂。
我们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
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临时的、被监管的房客。
她也不再把我当成一个需要提防的危险人物。
我开始主动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。
劈柴,挑水,修补漏雨的屋顶。
我的身体很瘦弱,干这些活很吃力,经常弄得自己腰酸背痛。
但每次看到她接过我挑来的水时,嘴角那一闪而过的、淡淡的笑意,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。
她的话依然不多,但我们之间开始有了真正的交流。
她会告诉我,哪种蘑菇有毒,哪种草药可以治跌打损伤。
我会告诉她,山那边是什么样子,城里最高的楼有多高。
小山也不再那么怕我了。
他会偷偷地看我读书,小脸上满是好奇。
我开始教他认字,念唐诗。
我没有纸笔,就用树枝在地上写。
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”
我念一句,他跟着念一句,声音稚嫩,却很认真。
林水云就在一旁,一边缝补衣服,一边静静地听着。
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进来,给她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
那一刻,我产生了一种错觉。
仿佛我们不是两个被命运随意抛掷到一起的陌生人,而是一个真正的家庭。
一个残缺的、临时的、却又带着一丝暖意的家庭。
这种感觉让我感到恐慌,又有些贪恋。
我知道,这是不应该的。
我还有妻子,有孩子在城里等着我。
虽然在我出事后,妻子为了划清界限,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联系了。
但我不能,也不该,在这里产生任何不该有的念想。
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,把对她的感激和亲近,都定义为“革命同志般的互助”。
但有些东西,是克制不住的。
尤其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,两个孤独的灵魂,太容易互相取暖。
那天,养殖场的鱼出栏,分给我和她几条。
她做了满满一大锅鱼汤,奶白色的,鲜美无比。
她给小山盛了一大碗,也给我盛了一大碗。
“多吃点,补补身子。”她说。
我们三个人围着小桌子,喝着热腾腾的鱼汤。
屋外是清冷的月光,屋内是温暖的灯火。
小山吃得满嘴是油,开心地笑着。
林水云看着他,眼神里满是慈爱。
然后,她抬起头,看了我一眼。
她的目光在灯光下,亮得惊人。
那一刻,我读懂了她眼神里的东西。
有感激,有依赖,还有一种更深沉的、我不敢去触碰的情感。
我的心猛地一跳,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。
我仓皇地低下头,假装专心地喝汤。
但我知道,有些东西,已经不一样了。
那道无形的墙,在不知不觉中,已经消失了。
我们之间,只隔着那道薄薄的、象征性的布帘。
日子在平静中一天天流过。
春去秋来,水库边的野花开了又谢。
我在这里已经待了快三年了。
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
习惯了每天听着水声醒来,习惯了吃她做的粗茶淡饭,习惯了教小山念“床前明月光”。
我甚至开始觉得,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,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城里的风风雨雨,那些倾轧和斗争,似乎都离我很远了。
在这里,我只是一个看守闸门的陈敬明。
一个能帮林水云挑水劈柴,能教小山认字的男人。
这种简单和纯粹,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宁。
我和林水云之间,依然保持着最后的界限。
我们睡在各自的“房间”,中间隔着那道布帘。
但我们的心,却在一天天地靠近。
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言语的默契。
她一个眼神,我就知道她是累了,还是心情不好。
我一声咳嗽,她就会默默地给我端来一杯热水。
我们就像两棵生长在悬崖边的树,为了抵御风雨,根系在看不见的地下,紧紧地纠缠在了一起。
村里的流言蜚语从来没有断过。
王主任也找我谈过几次话,警告我“注意影响”,“不要犯生活作风的错误”。
我只是沉默地听着。
我知道,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。
在这个非黑即白的世界里,没有人会相信男女之间存在纯洁的友谊,尤其是在我们这种“成分不好”的人之间。
有一次,村里几个爱嚼舌根的女人,当着林水云的面,说的话很难听。
“一个寡妇,一个坏分子,天天待在一个屋里,能干出什么好事?”
“看她儿子,跟那个姓陈的长得越来越像了。”
小山当时就在旁边,听到这话,气得捡起石头就想砸过去。
林水云一把拉住了他。
她没有哭,也没有骂,只是冷冷地看着那几个女人。
“我林水云行得正坐得端,”她说,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,“你们要是再敢胡说八道,我就去公社告你们,告你们破坏对‘改造人员’的监管工作!”
那几个女人被她的气势镇住了,讪讪地走了。
晚上,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水边,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我走过去,在她身边坐下。
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。
“对不起,”我低声说,“是我连累了你。”
她摇摇头,擦了擦眼泪。
“不怪你。”她说,“这世道,本就容不下我们这样的人。”
她转过头,看着我,月光下,她的眼睛像两汪清泉。
“陈敬明,”她第一次叫我的全名,“你是个好人。我知道。”
“水云……”我喉咙发紧。
“别说了。”她打断我,“我什么都明白。你和我们不一样,你迟早是要走的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静,平静得让我心疼。
“我走了,你和小山怎么办?”我忍不住问。
她沉默了很久,才轻轻地说:“我们有我们的命。”
那一晚,我们聊了很多。
聊她的丈夫,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,是如何在修水坝时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。
聊我的妻子,那个曾经和我一起吟诗作对的大家闺秀,是如何在我出事后递上离婚申请书的。
我们像两个溺水的人,互相倾诉着彼此的伤痛,以此来汲取一点活下去的力量。
夜深了,水面起了雾。
“回去吧,冷。”我说。
她站起来,走了两步,又停下。
她转过身,看着我,忽然问:“陈敬明,如果……如果没有以后,你会不会……愿意留下来?”
我的心像被重锤击中。
我看着她,看着她眼里的期盼和脆弱。
我多想说“我愿意”。
但我不能。
我不能给她一个我无法兑现的承诺。
我沉默了。
她眼里的光,一点点地暗了下去。
她自嘲地笑了笑,“我胡说什么呢。回去吧。”
她转身,走进了那间小泥屋。
我看着她的背影,感觉自己的心被撕成了两半。
那一晚,我第一次失眠了。
我躺在床上,反复问自己:陈敬明,你到底想要什么?
是回到那个已经物是人非的城市,去争一个虚无缥缈的“平反”?
还是留在这个贫瘠但真实的地方,守护这一灯如豆的温暖?
我没有答案。
一九七九年春天,一封来自北京的信,打破了水库的平静。
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寄来的。
信上说,形势变了,很多冤假错案都在平反。他正在帮我活动,让我无论如何要抱有希望。
我拿着那封信,手微微颤抖。
希望。
多么奢侈的一个词。
我把信给林水云看。
她看得很慢,很仔细,仿佛要看懂每一个字。
看完后,她把信还给我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“这是好事。”她说。
“如果……如果我真的能回去了……”我看着她,试探地问。
“那就回去。”她打断我,语气很平静,“你本就不属于这里。”
我心里一沉。
我原以为她会有些不舍,或者至少会问我,回去了还会不会记得她。
但她没有。
她表现得比我还冷静,还豁达。
接下来的日子,她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我。
她不再等我一起吃饭。
她也很少再和我说话。
我们之间,仿佛又回到了最初那种相敬如“冰”的状态。
我心里很难受,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
我能感觉到,她是在用这种方式,逼着我离开,逼着我斩断对这里的眷恋。
她越是这样,我心里就越是挣扎。
终于,那一天还是来了。
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水库,带来了我的平反通知书。
我恢复了名誉,恢复了工作,可以立刻返回北京。
王主任握着我的手,满脸堆笑,说着“恭喜恭喜”。
村里的人也都围过来看热闹,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敬畏。
我像一个被簇拥的英雄。
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
我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,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她不在。
我跟王主任请了个假,说要回去收拾东西。
我跑回那间小泥屋。
她正在灶台前,给小山做饭。
我的行李已经被她收拾好了,就放在门口。
里面除了我的书和衣服,还多了一个布包,沉甸甸的。
我打开一看,是晒干的鱼干和一些山里的干货。
还有一双崭新的布鞋,鞋底纳得密密麻麻,针脚细密得让人心疼。
“水云。”我叫她。
她没有回头。
“车在等你了,快走吧。”她的声音闷闷的。
“我……”我走到她身后,想说点什么,却发现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。
我想说,等我回去安顿好了,就来接你和小山。
我想说,这三年的恩情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我想说,其实我……
但这些话,在她的沉默面前,都显得那么虚伪和无力。
小山从屋里跑出来,拉着我的衣角,仰着头问:“陈叔叔,你要走了吗?”
我蹲下身,摸了摸他的头。
“叔叔要回城里了。”
“你还会回来吗?”他问,眼睛里满是不舍。
我看着他酷似林水云的眼睛,心如刀绞。
“会的。”我说,“叔叔一定会回来看你的。”
我说这话的时候,不敢去看林水云。
我怕看到她失望的眼神。
吉普车的喇叭声在催促。
我必须走了。
我站起来,最后看了林水云的背影一眼。
她依然背对着我,肩膀瘦削,倔强地挺立着。
我咬了咬牙,转身走出了那间我住了三年的小泥屋。
车子开动的时候,我从后视镜里看到,她终于追了出来。
她没有哭,也没有喊。
她只是抱着小山,静静地站在路边,看着我的车越开越远,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。
那一刻,我终于忍不住,泪流满面。
回到北京后,我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。
补发工资,分配住房,恢复职称。
一切都像一场梦。
我试图联系林水云。
我给她写信,寄钱,寄粮票。
第一封信,她回了。
信是小山代笔的,字写得歪歪扭扭。
信上说,她们都很好,让我不要挂念。钱和票都收到了,但以后不要再寄了,她们自己能过活。
我看了信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我继续写,继续寄。
但那些信,都如石沉大海,再也没有回音。
后来,我娶了现在的妻子。
她是我的同事,一个温婉的知识女性。
我们有共同的语言,相似的经历。
我们的结合,更像是一种抱团取暖,一种对安稳生活的妥协。
我跟她坦白过在水库的那段经历,但隐去了很多细节。
我只说,那是一个善良的农妇,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。
妻子很通情达理,她说,有机会我们应该去看看她,报答她的恩情。
我说好。
但这个“好”字,一拖就是三十多年。
我忙于工作,忙于评职称,忙于带学生。
我把那段记忆,连同那个叫林水云的女人,一起尘封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。
我告诉自己,她可能已经改嫁了,有了新的生活。
我告诉自己,我们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,不联系,对她才是最好的。
我用这些理由来说服自己,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。
我以为,我已经把她忘了。
直到今天,这个来自南方的包裹,像一把钥匙,重新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
洪水滔天。
我坐在书房里,手里攥着那枚粗糙的木鱼,看着照片上她平静的脸。
我的妻子走了进来,给我披上一件外衣。
“老陈,怎么了?看你脸色不对。”
我把照片递给她。
她看了看,有些疑惑,“这是……”
“她叫林水云。”我说,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,“是……是当年在水库照顾我的那个人。”
妻子愣住了。
“那这个孩子……”
“是她的儿子,小山。”
“这个包裹是谁寄来的?”
我摇摇头,“我不知道。”
我拿起电话,颤抖着拨通了青龙山水库管理处的电话。
电话号码是我多年前托人要到的,一直存在本子里,却从来没有拨过。
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。
是一个年轻的声音。
我报上我的名字,说我想找一个叫林水云的人。
对方说他不知道,要去问问老主任。
过了很久,电话那头换了一个苍老的声音。
是当年的王主任。
“是陈教授啊!”他的声音又惊又喜,“哎呀,都这么多年了!”
我们寒暄了几句。
我终于忍不住,问出了那个我最想知道的问题。
“王主任,林水云……她现在怎么样了?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长久的沉默,让我心一点点地往下沉。
“老陈啊,”王主任的声音变得很沉重,“你……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“她……她不在了。”
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
“什么时候的事?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。
“走了有五年了。”王主任叹了口气,“癌症。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了,没受多少罪。”
“她……她后来……结婚了吗?”
“没有。”王主任说,“你走后,她就带着孩子离开了水库。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直到几年前,她病重了,才托人把骨灰送回村里,安葬在她男人旁边。”
“那……这个包裹……”
“是她儿子寄给你的。”王主任说,“这孩子,叫水生。林水云给他改的名。他说,是你的姓,加上她的名,陈水生。”
陈。水。生。
我的眼泪,终于决堤。
“她走之前,留了话。”王主任的声音在电话那头,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“她说,让你不要愧疚。她说,你当年承诺会回来看她,她信了。她等了你一年。后来不等了,不是不信了,是想通了。”
“她说,你是一条要游回大海的鱼,那个小水库,留不住你。她要是把你硬留下,就是害了你。”
“她还说,她这辈子,最高兴的事,就是认识了你。因为你让她儿子认了字,读了书。她说,有了文化,孩子就不会像她一样,一辈子困死在山里。”
“那个包裹里的东西,是她亲手给你准备的。那条木鱼,是她男人留下的遗物,她一直带在身上。她说,送给你,就当是个念想。”
“最后……最后她托她儿子转告你一句话。”
王主任顿了顿,仿佛在酝酿情绪。
“她说:陈敬明,青龙山的水是冷的,但你住过的那间屋子,灯是暖的。我不怨你。每个人,都有自己要渡的河,要上的岸。”
我再也控制不住,失声痛哭。
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,在自己的书房里,哭得像个孩子。
我哭的,是她的苦。
我哭的,是她的善。
我哭的,是我的懦弱和自私。
我以为我给了她希望,其实我给了她更深的绝望。
我以为我离开了是对她好,其实我是最残忍的逃兵。
她用她的一生,原谅了我的背叛。
她用她的沉默,守护了我可笑的尊严。
我欠她的,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
挂了电话,我枯坐了很久。
妻子一直默默地陪着我,给我递上热茶。
“老陈,”她轻声说,“王主任把她儿子的电话给我了。”
我抬起头,看着她。
她的眼神里没有责备,只有理解和同情。
“打一个吧。”她说,“有些事,总要面对。”
我看着桌上的那张纸条,上面写着一串陌生的号码。
陈水生。
我的……儿子。
不,我没有资格这么叫他。
他是林水云用一生的苦难,独自浇灌长大的树。
我只是那个,曾经在他生命里,短暂地投下一片阴凉,然后又匆匆离去的过客。
我拿起电话,手指却重如千斤。
我该跟他说什么?
说对不起?
三十多年的亏欠,一句“对不起”又有什么用?
我深吸一口气,终于按下了那个号码。
电话通了。
“喂,你好。”
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,沉稳,有礼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南方口音。
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
“你好,”我说,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,“我……我叫陈敬明。我收到了……你寄来的包裹。”
电话那头,沉默了。
我能听到他略显急促的呼吸声。
良久,他才开口,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
“陈……叔叔。”
相关推荐
- 看书网站哪个好用(看书比较好的网站)
-
1、起点中文网。2001年创办,2004年被盛大公司收购,成为盛大其他的文学类网站。起点中文网是国内最大的原创文学网站,“起点”这个名字也正是原创之意。2、小说阅读网。2004年创办,在刚成立的时候就...
- 幻之盛唐txt精校下载(幻之盛唐好看吗)
-
有五个,梁笑,考古学家,肉身穿越到安史之乱时期,混进了禁卫军队伍。与叛军大战之前,主角抄梅岭三章和秋瑾的诗。破长安之后逃亡蜀道,先是在马嵬坡救下了杨贵妃,成功护送李隆基入蜀,后又力挽狂澜平定内忧外患,...
- 郭敬明作品集 [共35本]-第1页,作者:郭敬明-爱下电子书
-
郭敬明文学帝国的陨落史长不大的孩子和他的欲望——郭敬明解析(上)一、词语、意象的拆解与拼装郭敬明坦言,他最喜欢自己的散文作品,并把散文写作的...
- 战恋雪 (凤舞)最新章节_战恋雪全文免费阅读_书香小说网
-
小说:挑战帝皇权威,他得到了这天下,却失去了自己最喜欢的女人对于梦西瑶取胜,顾乘风一点都不奇怪。付行舟的实力有多少,他也很清楚,在聚仙楼上对过两招,付行舟的实力也只是比普通的同境界强上一些。他跟楚若冰...
- 《重修之灭仙弑神》_txt全集下载_在线全文阅读 - 玄幻魔幻 - 爱上阅读
-
弑神灭仙1.《逆天邪神》by火星引力字数:万+背景:云澈为破神脉禁锢自废玄功,引九劫轮回之力重筑混沌之体。茉莉:他散尽神君修为时,天下骂他疯了。我看着他以凡人之躯重撕天穹,血染白衣却笑问:“谁说逆...
- 藏地密码(1-6部小说合集)txt下载 - xiashuwebnet
-
奇书,天书,还是假书央视网消息: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月9日至日举行。本届全运会从场馆建设、能源保障、赛事组织等各环节采取减碳措施,将打造历史上首届“碳中和”全运会。广东赛区共有个场馆,超过%是现有场...
- 恶魔总裁的囚宠_恶魔总裁的囚宠全文阅读_恶魔总裁的囚宠无弹窗在线阅读_总裁小说网
-
小说:她成为总裁的十日情人,他:折磨吗?她:你对我像公主一样你又点进来啦,是书荒了吗?关注我你每天都有不同风格的小说可以看哦。今日小说推荐:虐文:为了白月光,他将她送进监狱折磨了5年,又开始追妻火葬场...
- 霸爱出墙拽公主在线阅读(莫、凉悦)_去读读
-
女主抱大腿文大合集,穿成炮灰女配,为了苟活,无奈开启狗腿日常|关注腹黑的白米饭,带你告别书荒!今天分享几本追妻火葬场文,剧情很精彩,文笔好!男主一开始爱搭不理,后面深深打脸,先虐后甜,暧昧拉扯,追妻路...
- 绝世赘婿叶昊免费完结版(绝世赘婿叶昊免费完结版下载)
-
叶昊郑漫儿大结局是4985章,主要讲,三年前,叶昊他是叶家世子,却遭家族赶尽杀绝,濒死之际,为她所收留。三年后,他已是军中神话,大夏传奇!
- 必看十大穿越剧2025(必看十大穿越剧赵露思演的)
-
《亲爱的吾兄》《满月之下请相爱》《第二次初见》1、《你好,李焕英》《你好,李焕英》现正在电影院上映,影片中女主李焕英原型就是贾玲的母亲,电影是根据几年前贾玲创作的同名小品改编的。影片中贾玲穿越到母亲年...
- 《桃花村的女人》_桃花村的女人最新章节_17楼新书_咖啡小说网
-
娇美村花刘喜妹的情路(1)初遇刚订了婚的王会计东方刚刚破晓的时候,声声唢呐,夹杂着欢天喜地的喧腾,村子里最美丽的姑娘桃花,被一个面孔稚嫩的小伙子背进了林成家。那桃花,长得就像是盛开的一枝花,犹如那三...
- 我只喜欢你电视剧免费观看(我只喜欢你电视剧免费观看25)
-
王语然退学后就没有再交代她的事。言默突然聊起了赵乔一最喜欢的周杰伦,并约赵乔一去看电影。赵乔一与言默看完电影后,两人意外碰见王语然。孙振奇因追求王语然失败,便把王语然摆小吃摊的照片贴在黑板上,王语然被...
- 《同居万万岁》txt全集下载-夏天以后 电子书txt全集下载
-
9本熟男熟女,成年人的爱情好带感!谁先入了心?本报记者高敏通讯员丁海芳本报讯同居两年,重庆姑娘小李没有察觉到,和自己朝夕相处、同床共枕的“男朋友”居然是个女人!与此同时,龙泉男子小郭也没料到,...
-
- 繁星中文网(女校全文免费阅读繁星中文网)
-
繁星中文网是一个小说阅读和作者写作的公司网站平台,隶属于杭州摘星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。该平台提供了大量的小说作品,涵盖了各种类型和风格,包括都市职场、武侠仙侠、现代言情、玄幻奇幻、星榜推荐等。此外,繁星中文网还为作者提供了一个写作平台,让更多...
-
2025-10-27 15:37 itomcoil
- 恶灵国度 (弹指一笑间0)_恶灵国度无错完整版_恶灵国度最新章节_笔趣阁
-
两篇前半部可封神的恐怖惊悚黑暗文,评价一下那篇更精彩?喜欢惊悚文的读者,应该都知道在惊悚文界有两位大神,黑色火种和弹指一笑间,两位作者在构思脑洞方面绝对是恐怖小说一流的,烧脑刺激惊险,今天各推一篇,大...
- 一周热门
-
-
都市之纨绔天才txt全集下载(都市之纨绔天才校对版)
-
《太平天国》(史景迁) 小说免费阅读-聚小说
-
第103部分-重生校草艳遇江湖 - 发发文学
-
十大生存类手机游戏(生存类游戏 手机)
-
好看的gl小说(好看的gl小说古代推荐豆瓣)
-
穿越好事多磨-吱吱-穿越好事多磨小说全文免费在线阅读-28看书网
-
徐方郑秀兰_醉不乖_徐方郑秀兰小说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吾看书
-
网游-屠龙巫师txt下载,网游-屠龙巫师txt全集下载,网游-屠龙巫师全本完整版免费下载 - 365小说网
-
激浊扬清(激浊扬清的近义词)
-
他似火 (军婚 高干 婚恋)最新章节_他似火 (军婚 高干 婚恋)全文阅读_他似火 (军婚 高干 婚恋)全本免费阅读-TXT电子书下载 -肉肉屋
-
- 最近发表
- 标签列表
-